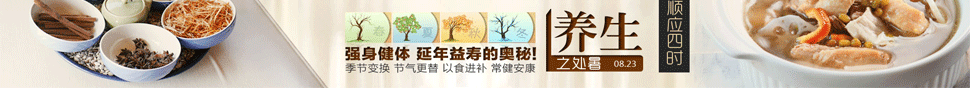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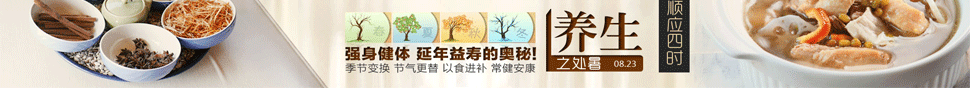
有部电影,叫《道士下山》,一个道士从清修到红尘,遇到的是一劫又一劫,钱、情、病、贫、苦……幸福和满足是短暂的,虚幻的……执迷是最无可救药的病,好比被牵着鼻子的牛,执迷就是“下山”,醒悟就是“入山”。而从红尘到清修,是一个化苦为甜的过程。
看起来两者都很好,但现实中很难两全其美。
港台武侠小说里的“入山”,和现实中“入山”不同,武侠小说里“入山”是为了拜名师、找宝典,有了这些,就可以给君王做参谋,龙云虎风,影响时代,报效祖国……可是众多门派掌门整天呼风唤雨,行走江湖,可以说比凡夫俗子都忙、都热闹,既争名又争利,既为情仇恩怨,又为家国大义……
吊诡的是,武侠小说里,凡是奉着主义和形态要“一统江湖”的都是反派,坏蛋,凡是反对“一统江湖”的,往往最后都是主角。
历史上这种模式也不是没有,最典型的是三国。
事实上,真正的“入山”不是为了成为英雄和人杰,而是为了真的了却红尘,在凡人眼里,“入山”标志俗人变得更俗(了却欲望带来的争斗和烦恼),选择自主消失、自动回避。
真实的“出山”,其实也是鸡毛蒜皮,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丰功伟绩拿人头和命大去换的(不干不净的术),绝不是学个绝世武功就可以一统江湖。“出山”后生存不易,至于发展更是道路曲折,基本由老天决定(一命二运之牙慧)。所以历史上鬼头鬼脑想当皇帝的人不计其数,但都不敢露头,造反往往忌讳打率先打旗号,率先打旗号的都率先消失。
现实中游走于“出山”和“入山”之间的人,几乎没有,张三丰和济公也是半传说中的人物。丘处机确有其人其事,但并不是神神叨叨只会画咒的。今天“入山”学道,明天“出山”召开武林大会,后天又“入山”深造……古往今来无人可以做到。
华山峨眉又不是清华北大,有悬崖峭壁没有盖世秘籍。今天即便你进最好的学校学最好的科技,都不可能马上建功立业,何况交通靠走、说话靠吼、消息传2里就变谣言的古代?
出入之间,是一道无形的墙。
你去旅游景点看看,徘徊庙门的人不计其数,但踏入门槛的少之又少。或者身似乎已经“入山”,心却一直在“出山”,或者自以为心已经“入山”,又无法以身相入,也不是真的“入山”,这玩意是真的难。
“出山”和“入山”是中国人最古老的话题,早到姜子牙时代,传说昆仑山和中原是圣与俗的两个代表。姜子牙生前有没有去西藏青海,住世界屋脊,可以推导和探讨,但如今环境严酷的昆仑山和传说中众仙居住的瑶池仙境(非地球)毕竟现实和理想相差太远。
姜子牙入山得道,出山得天下,这个模式太诱人。春秋战国中国脑细胞发达的人出来一大堆,其中道家主张“入山”,儒家主张“出山”,以至于传说中老子也骑牛西入函谷关,不知所终。
昆仑山,就像15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印度和中国,富饶堂皇,好比马尔代夫、黄山、潘多拉星球的混合体,仙人们踩着云彩忙着摘果子,值得冒险和远征,可真正接触之后却失望至极,是冻土、荒漠和无人区。
历史上江河日下,秦始皇被徐福骗了,历代皇帝吃的仙丹都是汞丸,后人对“求道”渐渐失去兴趣,中原越来越繁荣,昆仑山越来越被人认为不可信(我们寄予希望的月亮也只是一块寂寞的大石头)。唐朝时不少人进终南山隐居,只是为了留下高隐卓居的名声,皇帝听到会给个大官,这叫做“终南捷径”,隐居是假隐,为求官而求道,人民又一次骗了皇帝。这条路比苦哈哈读书,一级一级考科举,或进部队去边疆锻炼写战场诗歌凑效多了。
人人都觉得人生太短,短到来不及求道,姜子牙80岁才下山辅佐文王,应该大半辈子都在山里度过了,对于多数人而言,得真道太慢,没个两三百年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生仓促,人人争着吃喝、争夺、婚娶、养育,还要鞭打脚踢让下一代赢在起跑线上。下一代再作践下下一代……
李白也想成为姜尚、子房、诸葛亮这类人物,但他一生游弋不定、塞北江南,注定无法有高居一阁,看清世态的能力,也就是爱世界不爱真理,晚年差点因为幼稚病在牢狱中度过,自己亲自证明,游山玩水不是搞大事的料。成大事靠光明,也可以靠厚黑,但绝不可能靠无知。
“入山”是觉悟,“出山”是本能,非违反本能,逆其道而行者,不能说已经觉悟。一生沾在钱的蜜罐和名的糖浆里,像一只蚊子,有翅膀也飞不动,说话声却比飞机场的噪音都大,此山大,此山舒服,临走留下一个壳子。纵然百岁,也如同一瞬。
从“出山”到“入山”,中间都是苦,扫荡妖魔,踏平坎坷,但只须你认为值,别人眼里的苦就是你无比的甜。身为是非人,不在是非中,身在中原,心在昆仑,甜是甜,苦也是甜,想必此时就可称作,活明白了。
人生短短,急个球?一定要活明白,才能称得上对自己有个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