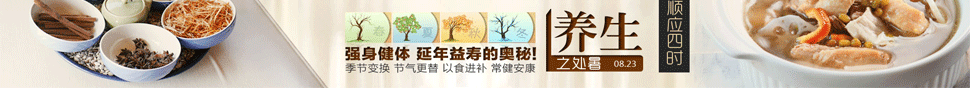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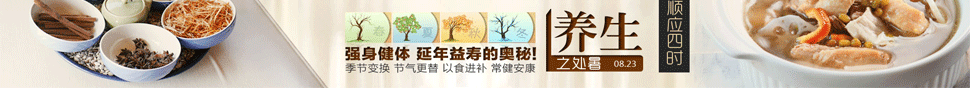
李兵,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付腾梓,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本文系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法律引入“被遗忘权”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编号16CXW)的研究成果。
“被遗忘权”(therighttobeforgotten)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一权利来自有犯罪前科或者污点人员的“被遗忘权”。个人信息“删除权”(therighttoerasure)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浪潮的成果之一。“被遗忘权”与“删除权”的并列提法源于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称《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
年3月,《条例》再次修订时,将原第17条中的“被遗忘权和删除权”(therighttobeforgottenandtoerasure)简化为了“删除权”。“被遗忘权”与“删除权”虽然以括号内和括号外的形式出现,其实在内容上完全重合,“被遗忘”说明权利行使的目的,而“删除”则说明实现权利的手段(刘文杰,:25-26)。由于“被遗忘权”的提法更普遍,为防疏漏和尊重原文,本文采通说“被遗忘权”。
本文以“therighttobeforgotten”“therighttodelete”“therighttoerasure”等为关键词检索SpringerLink、Jstor、Wiley-Blackwell、SAGEPremier全文数据库,TaylorFrancisST期刊回溯全文数据库,EBSCO大众传媒学全文数据库及两大法学全文数据库HeinOnline和LexisNexisAcademic等多个重要全文数据库,着重阐述英语学界“被遗忘权”研究聚焦的几个重点,并对学者争议比较集中的问题提出补充性的看法。
一
研究概况
年,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弗朗兹·沃尔(FranzWerro)发表题为《知情权v.被遗忘权:一个跨洋断裂》(TheRighttoInformv.theRighttobeForgotten:ATransatlanticClash)一文,是能检索到的集中讨论“被遗忘权”的最早研究。年1月末,欧洲委员会提议创设一种新的隐私权——“被遗忘权”,列入规划中的《条例》当中。伴随着欧盟的提议和大众讨论,学界关于“被遗忘权”的研究在-这两年开始批量出现。
年11月,欧盟出台《条例》,第17条增设“被遗忘权和删除权”,规定“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与其个人有关的数据,特别是当数据主体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时”。年3月,《条例》再次修订时,将其简化为“删除权”,并删除了对数据主体是未成年人的着重强调,规定“当用户依法撤回同意或者数据控制者不再有合法理由继续处理数据时,用户有权要求删除数据”。年4月,《条例》正式被欧盟委员会及欧盟议会通过,并在年5月25日正式生效。
其第17条是世界范围内对“被遗忘权”与“删除权”最明确的成文法规定。
在判例法方面,年5月,欧洲法院在《谷歌诉冈萨雷斯被遗忘权案》中判决,数据主体可以基于“被遗忘权”要求谷歌等搜索引擎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已在互联网上公开的“不恰当的、不相干的或不再相关的、超出其最初处理目的”(inadequate,irrelevantornolongerrelevant,excessive)的信息。
成文法的规定以及判例的确认,带来了“被遗忘权”研究在这几年的大爆发,并且一直持续至今。整体看,这些研究有以下几个主题。
二
含义的共识
与对其他话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不同,学者们对“被遗忘权”的含义有基本共识:其意为数据主体在特定条件下,有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有关其个人信息的基本权利,其本质是隐私权在数字时代的新变种。它来源于欧洲某些国家法律中承认的通常是有犯罪前科的人拥有的避免其犯罪历史被公开的权利。
沃尔年的文章中所讨论的主要是指有犯罪前科和污点的罪犯及其家属的“被遗忘权”。同时,作者已经观察到了数字时代的“被遗忘权”与其文中特定人群“被遗忘权”之间的某种联系。他提到,欧洲的隐私倡导者主张互联网用户应该有权利控制,可能的话,消除他们留在网页上的信息,谓之“被遗忘权”。同时,他还提到了年美国一桩有争议的案子。此案中,一名法国网络用户起诉谷歌,想删掉之前他留在网页上的个人信息,但未获成功。原因是谷歌服务器在美国境内,无需遵守法国法律(Werro,:)。
蒂尔堡法学院管理和技术教授贝尔特—亚普·科普斯(Bert-JaapKoops)提出了三种“被遗忘权”的含义,其一就是现在讨论最多的数字时代的“被遗忘权”。作者指出,在大数据背景下,在由数码指纹(digitalfootprints)——用户自己生产的数据和数码阴影(datashadows)——他人生产的关于用户本人的数据,主要是公共和私人组织收集和存储个人数据的数据库——这两种类型的数据所组成的信息时代,“被遗忘权”能保证当个人与其他人初识的时候,他人不会通过关于自己过去的某些因素,尤其是那些来自(遥远的)过去的、与当下的决定或者他人形成对自己的看法无关的数据来看待自己(Koops,:4)。这种很重要的利益,可能要以法定权利的形式来保护。
关于这一权利的溯源,赫罗纳大学公法部资浅研究员佩雷·西蒙·卡斯特利亚诺(PereSimo?nCastellano)认为,对承认“被遗忘权”的讨论并不新鲜,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个新背景下的旧事物。作者区分了“遗忘权”(therighttooblivion)和“被遗忘权”:“遗忘权”涉及的是对法庭记录的公共接近,指代一个因为时间逝去不应该被记住的历史事件或者犯罪记录,意味着为了重返社会以及不被过去的行为“穷追猛打”,个人限制对他们包含在犯罪或法庭记录中的个人数据的获取。但是新的“被遗忘权”不仅指这些,还包括试图通过不再允许第三方获取这些信息,在特定时刻使公共信息重新回到私密状态。当其个人信息不受时间限制地在互联网上散布,“被遗忘权”是数据主体不受其带来的偏见的一种保障(Castellano,:18)。
以上可知,“被遗忘权”又称“删除权”(迈尔-舍恩伯格,/),其含义是,当用户对曾经的某次张贴信息行为后悔,希望撤下它;或者对其他人生产的关于自己的信息持有异议时,互联网应该允许其删除这些信息。“被遗忘权”对于网络用户控制谁能获取他们的个人信息至关重要,它属于信息自决权(informationalself-determination),目的是使个人对其个人信息每一阶段的用途拥有控制权(迈尔-舍恩伯格,/:)。如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杰弗里·罗森(JeffreyRosen)所言,“被遗忘权”提出了数字时代的一个紧迫问题,在互联网上很难让自己的过去被忘掉,由于每一张照片,状态更新和Twitter发文永远存在云端。由于互联网记录所有、不忘记任何,使所有公民都面临着忘掉过去的困难,而这个困难以前只是有犯罪前科的人才需要面对的(Rosen,:89)。总体来说,这一权利的终极目的是“被遗忘”,手段是“删除”。
三
实践困境及负面效应
因为切中互联网“矢志不忘”这一特征,“被遗忘权”被认为对保护个人隐私有显著价值。但新闻界对“被遗忘权”的态度呈现审慎的悲观状态,“总体上说,对‘被遗忘权’的报道出乎意料得消极”(RosnayGuadamuz,:9)。一些评论家对把“被遗忘权”置于本与其平等的其他权利之上提出批评(Hakim,)。新闻界的消极可能是基于此权利与信息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天然冲突。学界也有人指出了该权利的诸多弊端。比如,弗兰齐乌指出,《冈萨雷斯案》的判决结果直接影响互联网用户对特定个人的信息获取度(Frantziou,:)。
这一类研究在-年逐渐增多,在年《冈萨雷斯案》判决之后呈井喷态势。在批评的声音中,以对“被遗忘权”的可操作性定义及相关法律概念的含义的质疑居多。比如,鲁汶大学法律与信息通信技术中心的杰夫·奥斯洛斯(JefAusloos)认为,虽然听上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权利,但是它在实践和政策上都有问题。而且会给数据控制者(公司)施加做决定的负担,从经济角度考虑是不受欢迎的(Ausloos,:8)。
总体来说,批评意见集中在“被遗忘权”在司法实践中的诸多掣肘,以及该权利的实施可能会对后续判决和网络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上。
(一)实践困境
1.模糊和宽泛的法律规定在法律适用方面,学者们对有关法律用语的语焉不详有诸多微词,这些质疑集中在“个人信息”(personaldata)和“数据控制者”(datacontroller)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所指上,他们认为《条例》和欧洲法院在《冈萨雷斯案》的判决中对这两个概念都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其适用范围太过宽泛,给后续判决遗留下了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
(1)个人信息
《条例》第4条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任何指向一个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主体”)的信息。该可识别的自然人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识别,尤其是通过参照诸如姓名、身份证号码、定位数据、在线身份识别这类标识,或者是通过参照针对该自然人一个或多个如物理、生理、遗传、心理、经济、文化或社会身份的要素。
按照这个定义,其不仅包括那些直接和一个人联系起来的信息,比如,家庭住址、公民身份证号码、个人财务数据......还可能包括那些导致数据主体身份被识别的间接信息。美国协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麦凯·卡宁厄姆(McKayCunningham)认为,这个定义宽泛且模糊。这一饱受争议的定义的可操作化特征是“包含型而非限定型的”(Cunningham,:),这种宽泛的定义对于法律的执行并无益处。
自年隐私权被提出以来(WarrenBrandeis,:-),对于其内涵和具体所指一直难以统一。而过去20年间技术的巨大变革又从根本上改变了隐私的概念(McGoldrick,),加之网络空间中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和私人空间的公共化平行进行(胡泳,:),这些使得本就模糊的隐私概念更加捉摸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宽泛的、列举式的概念并不利于澄清隐私和个人信息的确切含义。
此外,《冈萨雷斯案》中欧洲法院要确定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在像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上输入某个人的名字,由搜索结果组成的链接列表是否属于个人信息。法院的判决意见是肯定的,但却引起了极大争议。
欧洲法院判决的依据是“附加伤害理论”(Additional-HarmTheory):搜索引擎运营商对数据主体权利的损害独立并区别于原始网站发布者。这是因为当人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别人的名字时,“明显更容易”获得与此人有关数据的“结构概况”(structuredoverview),进而建立有关这个人的详细侧面像。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方式,如果没有搜索引擎,原本孤立的搜索结果并不能彼此关联。而这一“结构概况”会影响被检索者的私生活和个人信息保护。但法院这种对个人信息的扩张解释是反对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搜索引擎不能被当成数据控制者,因为它们是以一种偶然的、无差别的、随机的方式处理这些包含个人信息的链接(Frantziou,:)。
(2)数据控制者
《条例》第4条规定:“(数据)控制者”是能单独或联合决定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和方式的自然人、法人、公共机构、行政机关或其他非法人组织。
对“数据控制者”含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欧洲法院将谷歌这种搜索引擎当成数据控制者来处理,学者们认为搜索引擎不是数据生产者,在其身上施加执行“被遗忘权”的义务和责任是不合理的。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戴维·施图特(DavidStute)指出,对“数据控制者”宽泛的、“盲目的字面”解释可能导致搜索引擎本身就是非法的这一荒谬结果(Stute,:)。弗兰齐乌从商业方面考虑,这种对数据控制者的宽泛建构不仅会只影响谷歌,而且能将与网络信息有关的隐私侵权责任转移到大多数网络运营商身上(Frantziou,:)。对它们来说,这种过重的责任,不一定是适当的。
“数据控制者”所指涉过于宽泛。所有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出现在网页上的数据的网页所有者(webpageowners)都有义务承担因未删除相关数据导致的责任(Frantziou,:)。普通的互联网用户也要履行数据控制者的责任义务(Stute,:)。如果在所有这些不同情况之下都适用同样的“控制者”标准,在其他小型的网络运营商,甚至作为个体的网络用户身上施加和谷歌一样的责任,这将很难令人信服。基于以上考虑,让每一个网页所有者理解责任的边界就变得至关重要,但是欧洲法院没有界定这个权利的目标和内涵,因此给法律的实施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Frantziou,:)。
最重要的是,责任主体的扩大无形中置换了宪法权利的义务对象。如克瑞顿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凯利(MichaelKelly)等学者所言,欧洲法院开始认可对一种不仅针对政府部门,而且针对私人、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基本人权进行保护,保证宪法权利不仅像传统那样只限于对政府行为的限制,而要针对私人主体实施(KellySatola,:2)。
(3)其他不确定性
《条例》第3条规定适用范围采用属地和属人两种方式,将导致适用范围太广,大量公司和个人无辜受限,最终有碍欧盟的经济利益。对法律的逐字执行将把欧洲市场从国际经济中截断。基于此,《条例》不应把重点放在个人信息的“处理”或者“收集”上,而应该强调调整对个人信息的“不适当使用”(inappropriateuse)。比如,秘密监视、将其秘密传输给身份不明的第三方、通过交易将个人信息货币化(Cunningham,:)。
综合以上,虽然有了成文法的规定和判例的确认,但“被遗忘权”这个概念徒具修辞意义,缺乏可操作化的实践概念。“既然‘被遗忘权’是一个无定形的概念,当被用于维护一个人的声誉时,就使权利的平衡变得更加复杂”(Fazlioglu,)。苏黎世大学国际商法讲座教授及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罗尔夫·韦伯(RolfWeber)认为,这个概念太模糊以至于无法成功,必须为这一权利设想出一个真实的客体。仅仅对这一权利的宣告并不够,它需要在实践中被具体化(Weber,:)。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利蒂西娅·博德等(LeticiaBode)认为,“被遗忘权”的法律语言及其限制条款的规定是模糊的,因此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Bode,:77)。施图特进而建议,应该在地理范围、受影响的领域和要件、限制原则等方面对个人信息和“被遗忘权”进行清楚的界定(Stute,:)。
2.“史翠珊效应”
从实际效果看,“被遗忘权”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到互联网信息流动的独特方式,在网络空间实现“被遗忘”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史翠珊效应”(Streisandeffect)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它指越是试图阻止大众了解某些内容,或压制特定的网络信息,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使该事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即俗语说的“越描越黑”。基于开放和共享的本质,“史翠珊效应”广泛存在于网络空间中,使得“删除”和“被遗忘”在现实中难以奏效。
作为全球保护“被遗忘权”的首个案例,《冈萨雷斯案》本身就是“史翠珊效应”的最好说明。冈萨雷斯试图删除关于他年债务的报道,但是在年的某天,“全世界最大的媒体刊登了关于其债务的篇报道,包括在那些从未听说过他名字的国家和欧洲法院的判决不能影响到的地方。”现在,在谷歌上搜索冈萨雷斯的名字,会出现成千上万篇文章,将他与“被遗忘权”联系起来,最终指向他年的债务。冈萨雷斯试图压制信息的努力只是放大了它(Cunningham,:-)。作为首个“被遗忘权”标志性个案,其被过度放大的社会效应可能是导致“史翠珊效应”的主要原因。但在互联网上,还存在其他大量专业技术和网站印证着“史翠珊效应”的存在。
事实上,一旦欧洲法律要求从谷歌剥离什么内容,这些内容就会从其他替代渠道重回共享状态。比如,自从“被遗忘权”提出以来,一种新的独立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列出了从欧洲范围内的搜索引擎上被移除的网页(Rawlinson,:)。伴随着各种多样化的搜索平台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追踪并有意再版被擦除的信息(Cunningham,:)。
第二,当谷歌从搜索列表中将链接删除时,被删除的第三方将会把这一删除结果告知其用户。维基百科有一个基于对读者友好的透明度报告,现在这个报告上包含了基于“被遗忘权”的删除内容。当然,这个报告只提供被删除链接的网页信息,不会告知请求者和请求原因(RosnayGuadamuz,:8)。但即便这样,也会导致那些被请求删除的数据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存在,甚至公开的范围更大。
最后,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的深网(deepweb),通过一般的搜索工具检索不到。大量学术资源、图书馆和私人数据库存储其中。人们选择用深网浏览信息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隐私,它能阻止其他组织和个人监视、收集、贩卖用户信息。在这些网站上内容提供者和用户都是匿名的,很难想象“被遗忘权”怎样应用于这种情况(Cunningham,:)。
“史翠珊效应”及网络空间信息生产与分享方式为“被遗忘权”效力的发挥设置了技术掣肘,这些都很可能导致“被遗忘”的努力归为徒劳。
(二)负面效应
从实施后果看,“被遗忘权”将对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民主产生威胁,将审查责任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导致审查“私人化”。
1.对国家主权和民主的威胁
《条例》采用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并用的方式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了为欧盟内的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任何数据控制者。这种超国界、超疆界的适用范围会带来严重问题。比如一个德国人删除网络内容的请求不仅会导致在google.de上搜索结果的删除,也会导致google.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kasitelidq.com/kstlfz/5592.html

